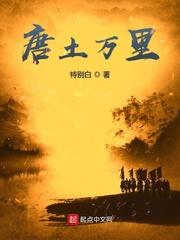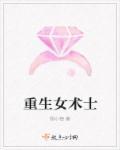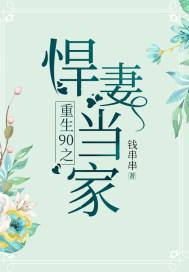手机浏览器扫描二维码访问
第167章 淯水烽烟(第1页)
第一百六十七章淯水烽烟
建安十四年夏,淯水河畔的麦田泛起金浪。陈果站在了望台上,望着柳如烟指挥百姓收割的身影,手中的《宛城安民册》被汗水洇湿一角。自收降张绣、逼退夏侯惇后,宛城已扩军至两万,粮仓里的粟米堆成小山,可远处汝南方向腾起的黑烟,却像一块烧红的烙铁,灼得人眼眶发烫。
“主公,探马急报!”张辽策马而来,铠甲上沾着未干的泥浆,“曹仁率五万大军南下,先锋官是……”他顿了顿,目光扫过台下正在教孩童识字的张绣,“是牛金。”
张绣手中的木笔突然折断。七年前宛城之乱,牛金曾奉曹昂之命镇守西寨,亲眼目睹胡车儿盗走他的虎头湛金枪。此刻他望着远处隐约可见的“曹”字军旗,喉结滚动:“末将愿带本部人马,驻守淯水渡口。”
“不可。”陈果按住他的肩膀,感受到对方肌肉紧绷如铁石,“牛金必会以‘旧怨’激你出战,曹仁却在等你乱了阵脚。”他转头看向马超,“孟起,你率三千铁骑绕后,截断敌军粮道;文远,你带陷阵营埋伏在芦苇荡,见火起便突袭中军。”
柳如烟抱着新绘的《淯水布防图》拾级而上,发间的木钗换成了一支竹制短笛:“主公可还记得,去年在许昌救过的沛国乐师?”她指尖划过图上“鹰嘴崖”标记,“那里回声悠长,若让乐师们吹奏《蒿里行》,牛金的骑兵必以为是鬼兵夜泣。”
陈果忽然轻笑,从腰间解下夏侯惇所赠的沛国玉佩:“就按如烟说的办。不过……”他望向正在给伤兵换药的徐晃,“公明,你曾与曹仁同守江陵,可知他安营扎寨的习惯?”
徐晃擦拭着腰间环首刀,刀身映出他紧蹙的眉头:“曹仁善用地形,必在淯水上游设了望塔,下游布铁蒺藜。但他有个癖好——每到新营,必命人在帅帐旁种槐树,说是‘怀祖德’。”
“怀祖德?”柳如烟忽然指着布防图上的槐树林,“若在那里埋火油,等东南风起……”
“妙!”陈果击掌而笑,目光扫过众人,“此战不仅要胜,还要让曹仁看清曹操的真面目。文绣,你随我去见牛金,记得带上……”他看向张绣腰间晃动的牡丹香囊,“曹昂公子的遗物。”
申时三刻,淯水渡口旌旗猎猎。牛金的赤马踏过浅滩,铁枪直指陈果咽喉:“叛将张绣也敢露面?当年若不是你……”
“牛将军可还记得,”张绣突然扯开衣襟,露出心口狰狞的箭疤,“这是曹昂公子替我挡的流矢。”他摸出香囊,丝绦上的牡丹纹样在阳光下泛着微光,“昨夜我梦见公子,他说‘叔侄一场,莫让刀刃向百姓’。”
牛金的枪尖微微下垂。他想起曹昂临终前,曾将张绣的降表藏在靴中,直到断气都紧攥着不放。远处,柳如烟的车队缓缓驶来,车上插着的不是军旗,而是密密麻麻的木牌,上面写着“曹军阵亡将士名录”。
“牛将军看看吧。”陈果抬手示意,车夫掀开竹帘,“这是从许昌偷运出来的密档,你麾下那八百沛国子弟,有多少是被曹操强征的?又有多少……”他声音陡然低沉,“死在征徐州时的‘人脯’营中?”
牛金的瞳孔骤缩。去年徐州之战,他曾亲眼看见粮车上装着陶罐,里面泡着的竟是……他猛地甩头,却听见芦苇荡中传来隐约的哭声,正是沛国丧礼上的《薤露》调子。战马受惊后退,蹄子踩中一块木牌,上面赫然写着“沛国牛氏祖坟已迁许昌义庄”。
“你……”牛金握紧缰绳,却见陈果身后的百姓突然跪下,为首的老汉捧着陶碗:“将军,我儿是你同村的牛二啊!他临出征前托人带话,说曹军的马料里掺了……”
“住口!”牛金怒吼,却看见老汉腕间戴着的,正是牛二成亲时打的银镯子。远处,马超的铁骑掀起漫天黄沙,“马”字大旗上的“威”字被夕阳染成血色。他忽然想起曹操lastmonth刚处决了沛国三名请免徭役的乡老,理由是“动摇军心”。
“牛将军,”陈果上前半步,声音放柔,“我在许昌建了‘洗兵堂’,凡弃甲归降者,可带家人入籍,分得三亩薄田。你瞧这淯水两岸,”他抬手掠过金黄的麦田,“百姓能吃饱饭,士兵能睡暖炕,难道不比跟着曹操屠城掠地强?”
牛金的铁枪“当啷”落地。他看见张绣正在给受伤的曹兵包扎,那些士兵脖子上挂着的,竟是陈军发放的“流民护符”。远处,柳如烟已带着乐师登上鹰嘴崖,竹笛声混着风声,竟像是无数亡魂在呜咽。
“末将……”牛金忽然下马,单膝跪地,“愿率先锋营归降,但求陈使君善待我沛国子弟。”
就在此时,淯水上游突然腾起冲天火光!曹仁的帅帐被火油引燃,槐树在烈焰中发出噼啪爆响,惊得战马四散奔逃。张辽的陷阵营从芦苇荡杀出,盾牌上的“义”字被火光映得通红,如同一面面滴血的战旗。
“中计了!”曹仁捂着被烟熏伤的眼睛,跨上战马时忽然看见,陈果正站在渡口高台,身后跟着的不是将领,而是一群抱着孩童的百姓。那些孩子手中举着纸糊的莲花灯,灯上写着“祈曹军退,愿五谷丰”。
“将军,粮道被马超截断!”亲卫的禀报被喊杀声撕碎。曹仁转头,看见自己的“虎豹骑”竟在麦田里寸步难行——不知何时,陈军已在田间挖了齐腰深的壕沟,里面插满削尖的竹桩。
“撤!往汝南方向撤!”曹仁挥动令旗,却听见身后传来熟悉的呼喊:“子孝兄!还记得当年在陈留,你我共饮的那坛菊花酒么?”
徐晃策马而出,手中捧着的陶坛正是当年曹仁所赠。坛口封泥裂开,酒香混着硝烟弥漫在空中。曹仁猛地勒住马,看着徐晃铠甲上的“陈”字徽章,忽然想起官渡之战时,此人曾冒死替他抢回被袁绍焚毁的粮草。
“公明,你……”曹仁的声音沙哑,独眼映着跳动的火光,“可曾后悔?”
“后悔未曾早日追随明主。”徐晃挺直腰杆,身后的陈军士卒正有序地将受伤的曹兵抬上木筏,“曹公若真为百姓,何必将徐州百姓赶尽杀绝?何必将屯田户充作‘人脯’?子孝兄,你我都清楚,他的眼里只有‘魏王’二字,哪有苍生?”
曹仁望着远处被陈军救下的曹兵,他们正捧着热粥狼吞虎咽,脸上不再有恐惧,只有劫后余生的庆幸。他忽然想起曹操在许都修建的铜雀台,那高达十丈的台基下,埋着多少百姓的骸骨?
“传令下去,”曹仁握紧马鞍,“留下断后部队,其余人……”他咬咬牙,“向陈使君开放汝南粮道。”
“子孝兄明智。”陈果不知何时已来到近前,手中托着一个木匣,“这是令堂去年托人带给你的冬衣,一直存放在许昌驿站。”
曹仁浑身剧震。母亲去年病重,他曾写信向曹操求助,却石沉大海。此刻打开木匣,里面除了棉衣,还有一封泛黄的家书,字迹是妹妹的笔迹:“兄归期未定,母常望南而泣,言‘阿满若成大事,需知民心比刀剑更利’……”
“陈使君,”曹仁抬起头,眼中已有泪光,“某有个不情之请——”他解下腰间的虎符,“若他日你兵临许昌,望能保我曹氏宗族中,未沾血腥者周全。”
陈果接过虎符,触感温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