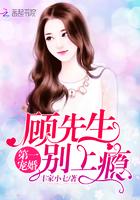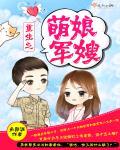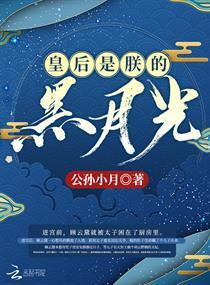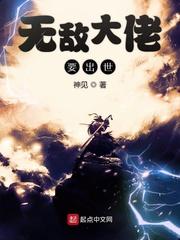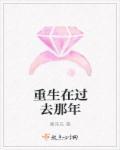手机浏览器扫描二维码访问
紫阳书(第1页)
探索求变·超越
——序陈平军《紫阳书》
秦兆基
陈平军先生的散文诗创作,一直在我的视域之内,看着他从《边走边唱》《好好爱我》写到《心语风影》,直到最近寄来的书稿《紫阳书》,前后垂三十年。“三十而立”,是一位作家由摸索逐渐走向自树,从人格精神到艺术技巧的阶段。
一
《紫阳书》确实使我看到在他过往的散文诗作中没有呈现过的东西,或者是作为潜质、隐性存在,并未显露出来而为读者感知的因素。这种变化使人欣喜。
诚如本书内容简介中所言:作者始终充满了尝试和创新、探索的精神,力求不重复自己,无论题材、修辞、结构、手法和风格等,都在不断求变。请注意两个关键词:“探索”和“求变”。探索,意味着进入未知领域;求变,意味着抛弃既成的格局,以新姿态傲视于人。探索与求变,对于一个作者来说,是一种艰辛的努力,也是心灵和艺术走向成熟过程中不可或缺的追求。如果以“探索”与“求变”为着眼点,细读文本就不难领略《紫阳书》的要义和艺术特色之所在,就不难衡量这部散文诗集在陈平军个人创作中的意义。
怎样才能感知和认识《紫阳书》中显示的“探索”精神和“求变”后呈现出的异象呢?
笔者在读《心语风影》后写过一段文字,似乎可作为解读《紫阳书》的参照系,那篇文字是这样写的:它(指《心语风影》)不像其他的散文诗作品那样视界开阔,涉墨成趣,只是默默地打量身边有限的世界:丰饶的陕南紫阳小城;生于斯,长于斯,蛰居于斯多年的山村白果;在油灯下默默批阅作业、备课的乡村小学屋舍;朝夕相处的家人,熟稔的乡亲……所有这些,构成了变动不居但幅度又不那么大的乡土社会的情境,亦即带着中国中西部特征的,——聆听到的、期盼着现代化的步伐的逼近,心想奋进而力有不能,焦躁不安而又转复平静。(《别样的视界和表述》)《紫阳书》,顾名思义,是在紫阳这方土地上抒写的,或者说是为这方土地上所曾有的和现实存在的一切——山岳、河川、建筑、物产、风习、观念形态、活着的和已经逝去的人们:家人、亲人、认识的和未必认识的人——而抒写的。就这点而言,陈君已经不再执着于抒写生于斯、长于斯的白果村、那所执教过的小学,那个可以视为历史见证的“端坐在白果村底部的石磨”,他从城里自己栖身的泗王庙巷走出,或是进入陈家老院,面对“超越宿命迁徙”的先人,心生愧意;或是去向汉江之滨,品赏错落有致的吊脚楼;或是来到徐家老宅,寻绎它的前世今生;或是与东城门对视,也算得上“相看两不厌”;或是历数瓦房店镇曾有过的会馆群:湖广的、福建的、江南的、浙江的……吊唁沦落异乡不得归去的亡灵;或是为了寻觅育婴堂的遗迹,去向泰山庙,理出有关愚人溺婴和善人救赎的那段历史;或是去悟真观,拜谒紫阳真人,就是那位给这方土地带来了华彩名字的道士;或是盘桓在大排档、钟鼓湾,在烟烧火燎、划拳痛饮,品尝“三转弯”“麻辣串”中,历练世情人生。陈君的足迹似乎还不止于此,他来到巴水和汉江的合流处,望云起云飞,看两水汇流激起的浪花;登神峰、凤岭,俯瞰紫阳大地。神驰文笔峰,董理自我痴情文学的万般情怀;涉淇水,神接卫国的贤君、淑妃卫武公、许穆夫人,沉吟于山旁泽畔的曹丕、王维、李白。
汇总起来,一方面,他从相对闭塞的山村走向灵动的诸水汇集、数省鸡鸣相闻的城市,散落的山川、村落和种种历史留存;一方面,他从熟稔的村民、亲人、天真的孩子走向市民、乡民,从他们的行为、话语走向心灵深处。
城镇是“人类社会权力和历史文化所形成的一种最大限度的汇聚体”(刘易斯·芒福德:《城市文化》),从城镇入手能更好地观照一方土地文明发展的程度和人们的精神状态。
很有意思的是,陈平军在对城市新貌和世态众生相的抒写中显示出社会的进步与沉滞。隧道,改善了城市的交通条件;快递,便利了商品流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维系着世道人心,构建了和谐社会。陈平军的诗笔既著录了紫阳这方土地上涌现的孝老养亲、助人为乐、敬业奉献、诚实守信、见义勇为的先进人物,留存了普通人的历史;又从一些习见的镜头中写出有的人精神猥琐、素质有待于提高的一面:泗王庙巷扫地的老大爷对乱抛垃圾者一日复一日的咒骂,麻将馆走出的老头、老太牌局得失的感慨,低头一族的学生妹、打工仔在手机游戏中的沉迷。
陈平军先生一段下乡工作的经历,既昭示着精准扶贫大趋势下,扶贫工作队员的作为和贫困户改变生存状态的强烈愿望的一面,又写出了某些农民积久形成的贪心、狡诈,卖弄小聪明的一面:子女在城里有豪车豪宅,老人还想再沾一点扶贫款去修老房,比穷、唠穷,甚至以穷为荣,作者的笔刺向我们民族集体无意识中的民粹主义残留。这种城市和乡村的沉滞,很容易使人想起鲁迅笔下生活在鲁镇、未庄的阿Q、王胡、小D,尽管一个世纪过去了,文学承担的精神启蒙的使命依然存在。
走向历史的那端,不止于行走,在过往的陈迹中怀想,还在于从文献中搜寻。陈平军比《心语风影》时期走得更远了,从落脚到紫阳的近祖溯向江州聚族而居的先祖,被唐僖宗褒奖为义门的,历数了这个家族经历的几个朝代中所发生的传奇:人的、动物的。描述了在宋仁宗敕旨下大家族被迫分崩离析的情景,《家谱记》就是这段历史的诗化演绎。笔者设想过在这种呈现中,是不是还可以更多点理性的审视,从社会历史的大背景下,予以深层次的考量。因为“只有从现在的最高力量的立场出发,你才有可能解释过去”(尼采),当代诗人可以而且应该有超越古人“一览众山小”的人文情怀,重释历史,实现诗性和理性的交融。
一切真的历史都是当代史,相因、相续、相承的传统与现实,期待着在陈平军的散文诗中会有泯然无迹的结合,实现更为完美的抵达。
二
“探索”与“求变”,不止于题材范围的扩大、立意的新颖,还在于表现方式的求新、求异,也就是“陌生化”的追求。前面提到的作者在“修辞、结构、手法和风格”等方面求变的追求,就属于这个范畴。
首先,要提的是结构的求变。结构是艺术家将内在的思绪外化为可感的艺术形象必不可少的一步,是决定作品成败的关键。清代戏曲家李渔,在他的理论作品中将结构经营放在最突出的位置上,提出“结构第一”,即将结构经营放在第一位。
散文诗与戏剧虽有所不同,不必追求戏剧语言的动作性和情节的环环相扣,但因为其一般比较短小,必须将诗的凝练和散文的形散神聚很好地统一起来,扩大作品的容量。陈平军在以前的散文诗中,往往有将笔墨过多集中于一点,用笔过重的地方。散文诗和写意画一样,细部与整体、意笔与工笔,要搭配得当,要做到“疏可走马,密不容针”。《从泗王庙巷进出》和《瓦房店吊脚楼》,很能显现陈平军结构经营的苦心孤诣,可谓“纳须弥于芥子”。
“二重唱”也不失为散文诗结构方式的创新,即每首散文诗前面有一首诗或者叙述性文字,类似旧体诗词的原作与和作、诗序与诗作的关系。文学作品最好不要只听作者一个人在叙述或吟唱,这种散文诗前加上一段他人的诗文,称得上是一种“复调”。
其次,要提的是修辞,广而言之曰——话语方式的求变。
《紫阳书》的笔致似乎放得开了。诗人只有懂得放纵与节制的协调,懂得什么场合该“惜墨如金”,什么场合该“泼墨如云”,才能创作出完美的画幅来。陈平军《在白鹤村徐家老宅烤火》中,有着很精彩的文字:
不过一切演绎都会经过黑漆漆
···
的夜晚的过滤,黑黢黢
···
的
“大烟筒”里黑黢黢
顾先生的第一宠婚
夏央央20岁的生日礼物是男友和闺蜜一起背叛了她她转身就和全城最金贵的男人顾祁琛领了证。从此一路打怪升级,所向无敌。...
重生之萌娘军嫂
黑心堂妹我要抢光你所以东西,包括你的男人无良老公你赚钱来,我来花,还在外面养娇花苏小晚痛彻心扉,天下怎么会有这种人?能赚钱有错吗?心地善良有错吗?...
热血狂兵
...
皇后是朕的黑月光
进宫前,顾云黛就被太子困在了厨房里。 进宫后,顾云黛一心想用药膳废了人渣。谁知太子妻妾迟迟无孕,她的肚子里却蹦了个儿子出来。 顾云黛本想母凭子贵安安静...
无敌大佬要出世
路一平是个上古修士,亲眼见证了诸神大战中,无数强大的神灵殒落的情景。自此之后,他便躲在深山老林,日夜修炼,发誓没有强大到对抗天地大劫的实力时,便不出来。一...
重生在过去那年
赵桐芸没想到,死亡不是终结,只是一个新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