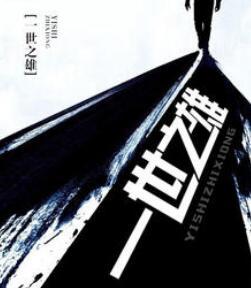手机浏览器扫描二维码访问
噬人宅九(第1页)
“是装的。”梁夜道。
海潮正在气头上,不防他突然这么说,就好像从浪头上掉下来,有些发懵:“啊?”
“方才那副样子,是我装的,”梁夜解释道,“那对夫妻有些古怪,我装出那副样子,是为了让他们轻视于我,放下戒心,关键时才能一击即中,看出他们真实反应。”
海潮用脚尖踢着路旁的小石子,嘟囔道:“跟我说这些做什么,莫名其妙。”
“怕你误会。”
“有什么好误会,”海潮抬头望望月亮,把一颗小石子踢得飞了起来,“说了你的事和我没干系。”
“嗯,”梁夜道,声音轻柔低缓,几乎像是在自言自语,“可还是怕你误会。”
海潮心里涌起股说不清道不明的滋味,最后却又化作酸涩。
三年前的梁夜不会说这种话,三年后……他们中间隔山隔海,还隔了个宰相千金。
夜风吹拂她的脸颊,有什么东西冷了下来。
“你刚才说那对夫妻古怪,哪里古怪?”海潮道,“我看他们郎才女貌,挺恩爱。就是那夫人有些死心眼。”
他们疍家女儿和男人一样出海捕鱼、下水采珠,不讲究什么以夫为纲,他们家说起来还是阿娘做主的时候多。
“幸好苏廷远待她一心一意,遇上个轻易变心的……”
她意有所指地瞟了眼梁夜:“可有的她哭的。”
“未必。”梁夜道。
“哎?”
“苏廷远未必可靠。”
海潮挑挑眉:“我看他挺着紧妻子的么,又体贴又耐心。”
许是因为父亲的缘故,海潮对于珍惜妻子的男人,总是天然带了几分好感。
她瞥了梁夜一眼:“也不是生得俊的都是负心汉,我看他不像坏人。”
她其实并没有觉得苏廷远有多俊,他的皮相在一般男子中算得拔尖,但海潮是看着梁夜长大的,和眼前月亮一样的少年郎比起来,寻常的俊俏郎君都失色了。
梁夜微垂眼帘,不见愠色,但那身影无端清寂了几分,像是今夜的冷月终于将他浸透了。
“是好是坏我不能断言,但他说了谎。”
“他什么时候说了谎?你怎么知道的?”
梁夜道:“因为他言行不一,有许多破绽。”
海潮回想了一下,实在想不出苏廷远的话里有什么破绽。
“反正我没看出来。”她道。
“你为何觉得苏廷远待他夫人好?”梁夜反问。
海潮一边回想一边说:“这不是明摆着的么?我们在院子里遇见他时,他多着急啊,还有我们去找他夫人问话的时候,他给夫人披衣、搀扶她的样子,一看就是平时做惯了的,说明他平常就是这么照顾他夫人的。”
梁夜:“那他为何要在前院书斋理账?”
“怕不是账册太多太重了?”
海潮旋即摇了摇头,她自己也觉这理由站不住脚,苏廷远又不是她,账册再多再重,也自有成群的奴仆给他搬。
“或者是担心吵到夫人?再怎么小心,总有动静吧……”这也说不通,苏家正院又不是她家小茅屋,怕打扰到妻子睡觉,去厢房不就好了。
两个厢房都很宽敞,还用帷幔隔出了斋室,实在不必特地去书斋。
海潮有些泄气,嘟囔道:“说到底,他也不知道今晚他夫人会出事呀。”
梁夜摇摇头:“你可记得那婢女的话?他夫人数月来时常为噩梦惊醒。若换作是你,能否安心彻夜在前院理账?”
海潮心里已认同梁夜的说法,只是嘴上不愿承认:“这些都是你猜的。”
出乎意料,梁夜颔首:“确实,这些都是猜测。所以直到方才,我才能确定他在说谎。”
“方才怎么了?”
他们明明什么都没做,只是绕着苏府走了一大圈。
证道从遮天开始
穿越遮天世界,证道不朽。无限流,第一个世界略长。...
夫人别贪欢,傅总带千亿携子求入赘
盛以若与傅兆琛是假偶天成。她图他庇护。他贪她美貌。成年人的游戏取于利益,缠于欲望。三年情断。有人问盛以若,她和傅兆琛是什么感觉?身,心愉悦。有人问傅兆琛,他和盛以若怎么打发时间?日,夜贪欢。你我皆是俗人,应懂得难以启齿的往往不是感觉,而是感情。落魄美艳千金VS霸道矜贵阔少双洁1V1...
蛇骨
我出生时,左手腕上缠着一条蛇骨,骨刺深深插入肉中。十八年后,白水出现在我面前,许诺与我血肉相缠。可结果,却比刮骨更让我生痛。蛇骨性邪,可又有什么比人心更邪?...
大明第一臣
元末濠州城外,朱元璋捡到了一个少年,从此洪武皇帝多了一条臂膀。抗元兵,渡长江,灭陈友谅,伐张士诚。创建大明,光复燕云。我无处不在。从此洪武立国,再无遗憾。...
炮灰养女逆袭记
做了一辈子炮灰的周谷儿重生了,重生在她即将被养父卖掉的那一年。重生后的周谷儿表示,这一辈子她的命运要自己掌握,决不再任人宰割。且看她这个炮灰养女如何斗极品,发家致富,收获幸福。...
一世之雄
原生家庭的伤害有多大,或是自卑懦弱,毫无自信或是暴力成性,锒铛入狱亦或撕裂婚姻,妻离子散无数次痛彻心扉的感悟后,有的人,用一生来治愈童年有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